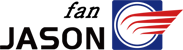- (0577)-55775657
- jason@jasonfan.cn
- Mon - Fri: 8am - 6pm
-
▓╚Í°ĚĘÁ┬í░▀^║Ëí▒ Íđç°đ┬─▄ď┤░l(fĘí)Ň╣┤ˇ═╗ç˙ üÝď┤ú║Ż▄ŕ╔áäŁ▓┐ ░l(fĘí)▓╝Ľr(shʬ)Úgú║2016/8/12 íííí─▄ď┤░▓╚źĎ╗Í▒╩ă▀M(jĘČn)╚Űđ┬╩└╝o(jĘČ)Ďď║ˇ
úČ╬Ďç°Ň■Ş«╦¨┤ˇ┴Ž│źîž(dĘúo)Á─íúË╔Ë┌▒ż═┴╩»Ë═íó╠ý╚╗ÜÔ«a(chĘún)┴┐▀h(yuĘún)▀h(yuĘún)đíË┌đŔăˇíúĎ╗Í▒ĎďüÝúČ│ř┴╦│źîž(dĘúo)▀M(jĘČn)đđÂÓď¬╗»▀M(jĘČn)┐┌═ÔúČç°â╚(nĘĘi)ĎÓ╚ŇĎŠÎóÍě░l(fĘí)Ň╣đ┬─▄ď┤«a(chĘún)śI(yĘĘ)íúđ┬─▄ď┤«a(chĘún)śI(yĘĘ)ŕP(guĘín)║§Íđç°╬┤üÝÁ─ĚÇ(wĘžn)ÂĘ║═░l(fĘí)Ň╣úČŞŘ╩ăśő(gĘ░u)│╔ç°╝Ď░▓╚źÁ─╗¨╩»úČ╩ăÍđç°«ö(dĘíng)ă░Á─͸Ϭç°▓▀Í«Ď╗íúíííí▒ěÝÜ▀M(jĘČn)đđÁ─í░đ┬─▄ď┤═╗ç˙í▒
ííííď┌鸯y(tĘ»ng)─▄ď┤ˇw¤ÁÍđ
úČ╬Ďç°îó─▄ď┤╗¨ÁA(chĘ│)ŻĘ┴óď┌âŽ┴┐│ń┼ŠÁ─├║╠┐Í«╔¤íúÍđç°ÄÎ║§╦¨ËđčßŰŐĆS┼cÂČ╝ż╣ę┼»¤ÁŻy(tĘ»ng)úČż¨Ď└┘ç├║╠┐íú╚╗°Îď╔¤╩└╝o(jĘČ)─ęĂúČŰSÍ°├║╠┐¤ű║─┴┐Á─╚ŇĎŠď÷╝ËúČ├║╚╝čřĽr(shʬ)«a(chĘún)╔˙Á─޸ţÉ┼┼Ě┼úČŇř╚ŇĎŠÉ║╗»Í°Íđç°▒▒ĚŻÁ─┤ˇÜÔşh(huĘón)ż│íúííííŻÔŤQ▀@éÇ(gĘĘ)ćľţ}Á─ŕP(guĘín)ŠI
úČď┌Ë┌Ň{(diĘĄo)Ňű╬ĎéâĎ╗Í▒ĎďüÝ─▄ď┤─ú╩ŻÍđúČ╚╝├║Á─▒╚└ř┼cśő(gĘ░u)│╔íú═ČĽr(shʬ)úČ├║╠┐θ×ÚĎ╗ĚNĚă│úâ×(yĘşu)đŃÁ─╗»╣Ąďş┴¤úČîóĂń«ö(dĘíng)θ╚╝┴¤░Î░ÎčřÁ˘Ď▓╬┤├Ô┐╔¤žíú┐╔ĎŐúČ▀@îó╩ăĎ╗ÝŚ(xiĘĄng)ŕP(guĘín)║§ç°╝Ďíó╔šĽ■╬┤üÝ░l(fĘí)Ň╣ă░═żÁ─ŕP(guĘín)ŠIŤQ▓▀íúíííí┤╦ă░░l(fĘí)Ş─╬»
íó─▄ď┤żÍ░l(fĘí)▓╝íÂŕP(guĘín)Ë┌┤┘▀M(jĘČn)╬Ďç°├║ŰŐËđđ˛░l(fĘí)Ň╣Á─═ĘͬíĚúČĂńÍđż═╠ßÁŻĎ¬ç└(yĘón)┐ě├║ŰŐ┐é┴┐ĎÄ(guĘę)─úúČŻ˝║ˇÁ─ĚŻ¤˛čoĎ╔╩ăđ┬─▄ď┤íú°ď┌Ż˝─ŕÁ─3ď┬│§░l(fĘí)▓╝Á─íÂŕP(guĘín)Ë┌ŻĘ┴ó┐╔ď┘╔˙─▄ď┤Ú_░l(fĘí)└űË├─┐ś╦(biĘío)Ďřîž(dĘúo)ÍĂÂ╚Á─ÍŞîž(dĘúo)ĎÔĎŐíĚÍđúČŞŘ├¸┤_ϬăˇË┌2020─ŕĽr(shʬ)úČĚă╦«ŰŐ┐╔ď┘╔˙─▄ď┤░l(fĘí)ŰŐ┴┐Ŭ(yĘęng)«ö(dĘíng)Ň╝┐é░l(fĘí)ŰŐ┴┐Á─9%íú°ď┌2015─ŕúČďô▒╚└řâHŇ╝╚źç°░l(fĘí)ŰŐ┐é┴┐Á─4.3%íú°▀@úČż═ĎÔ╬ÂÍ°╚˘¤Ű▀_(dĘó)ÁŻ─┐ś╦(biĘío)ät╬┤üÝ5─ŕ┐╔ď┘╔˙─▄ď┤░l(fĘí)ŰŐ┴┐─ŕĆ═(fĘ┤)║¤ď÷ÚL┬╩ÝÜ▀_(dĘó)18%íú▀@╩ăĎ╗éÇ(gĘĘ)Ěă│úŞ▀Á─öÁ(shĘ┤)ÎÍúČĎÔ╬ÂÍ°Ć─ČF(xiĘĄn)ď┌Ú_╩╝ż═Ϭ│Í└m(xĘ┤)żŮ┴┐═Â╚ŰíúÁź▀@úČĎ▓ż═ĎÔ╬ÂÍ°îóď┌ÍđÂ╠Ă┌â╚(nĘĘi)îŽç°â╚(nĘĘi)─▄ď┤─ú╩Ż▀M(jĘČn)đđ┤ˇÁ─Î⪴úČĂńÍđ│ńŁM┴╦´L(fĘąng)ŰU(xiĘún)║═ÎâöÁ(shĘ┤)íúíííí║├ď┌
úČ▀@Śl║ËĎĐŻŤ(jĘęng)Ëđ╚╦╠Š╬Ďéâ╠╦▀^úČÍđç°┤ˇ┐╔Ďď▓╚Í°í░╩»ţ^í▒▀^║Ëúíç°╝Ďđ┬─▄ď┤Ĺ(zhĘĄn)┬ď▀@Śl┤ˇ║ËÍđÁ─ë|─_╩»▀@â╔ëKí░╩»ţ^í▒úČĎ╗Ň▀├űŻđĚĘ╠m╬¸úČÂ■Ň▀├űď╗Á┬ĎÔÍżíúííííď┌┐╔ď┘╔˙─▄ď┤ţI(lĘźng)˲
íó─▄đžíóŻĘÍ■íóŻ╗═ĘţI(lĘźng)˲úČÁ┬ç°║═ĚĘç°Á──┐ś╦(biĘío)Ţ^×ÚĎ╗Í┬úČĂńł╠(zhʬ)đđŇ■▓▀Á─╣Ąż▀Ď▓ţH×ÚţÉ╦ĂíúĆ─â╔ç°Ň■▓▀îŹ(shʬ)█`┐┤úČÁ═╠╝╗»ŞéáÄÁ─║╦đ─ţI(lĘźng)˲ď┌Ë┌úČ┐╔ď┘╔˙─▄ď┤╝░ÜÔ║˛ËĐ║├đ═╝╝đg(shĘ┤)Á─═ĂĆVíó╩╣Ë├íúííííθ×Ú╣ĄśI(yĘĘ)ĆŐ(qiĘóng)ç°Á─Á┬ç°
úČË┌2004─ŕíó2009─ŕ║═2014─ŕĚÍäe╚ř┤╬đŮËćíÂ┐╔ď┘╔˙─▄ď┤ĚĘíĚúČÍ▓ŻŻÁÁ═Đa(bĘ│)┘NúČťp╔┘Íž│ÍŇ■▓▀úČ▓óďçłDĎř▀M(jĘČn)Şéś╦(biĘío)Á╚╩đł÷ŞéáÄÖC(jĘę)ÍĂíúÁ┬ç°┐╔ď┘╔˙─▄ď┤ÍđúČ´L(fĘąng)─▄íó╔˙╬´┘|(zhĘČ)─▄íó╠źŕľ─▄╬╗Ë┌ă░╚říú╚╗°úČ┘Yď┤üÝď┤Á─▓╗ĚÇ(wĘžn)ÂĘđďíóâŽ─▄╝╝đg(shĘ┤)Űyţ}íó┐╔─▄Á─şh(huĘón)ż│╬█╚żíó╔˙╬´ÂÓśËđďćľţ}úČŻo╬┤üÝă░ż░╠ß│÷┴╦ÍTÂÓáÄÎhíúď┌║╦─▄ĚŻ├ŠúČÁ┬ç°2022─ŕ║╦─▄═╦│÷Á─╠Š┤˙ĚŻ░Ş╚ďĹĎ°╬┤ŤQúČ18%Á─ŰŐ├║╩╣Ë├║╬╚ą║╬Ć─úČÂ╝ÍĂ╝s┴╦─▄ď┤ŮD(zhuĘún)đ═─┐ś╦(biĘío)Á─îŹ(shʬ)ČF(xiĘĄn)íúííííθ×ÚÜWÍŮŮr(nĘ«ng)śI(yĘĘ)┤ˇç°Á─ĚĘç°
úČď┌ŻŤ(jĘęng)Ł˙(jĘČ)¤┬đđÁ─ăÚŤr¤┬úČîŽË┌┐╔ď┘╔˙─▄ď┤╩ăĚ˝═¤└█ç°╝ĎŻŤ(jĘęng)Ł˙(jĘČ)úČĎ▓ţHż▀áÄÎhíúË╔Ë┌┐éˇwţA(yĘ┤)╦ŃżoĆłúČîŽ┐╔ď┘╔˙─▄ď┤Á─Íž│ÍĎÓď┌ťp╔┘íú┐╔ĎŐúČË╔Ë┌Íž│Í┐╔ď┘╔˙─▄ď┤Á─│╔▒ż▀^Â╚Ş▀░║úČÁ┬ĚĘâ╔ç°Ă¨Ż˝ż¨╬┤─▄▀_(dĘó)ÁŻţA(yĘ┤)Ă┌Á─╔šĽ■ŻŤ(jĘęng)Ł˙(jĘČ)şh(huĘón)ż│đžĎŠúČÚLĂ┌ŻŤ(jĘęng)Ł˙(jĘČ)Íž│ÍŇ■▓▀ŰyĎď×Ú└^íúíííí°ĚĘÁ┬â╔ç°îŽË┌鸯y(tĘ»ng)─▄ď┤ˇw¤ÁÁ─ĹB(tĘĄi)Â╚úČĎ▓╩ăÍÁÁ├Íđç°╝ËĎďĚÍ╬÷║═ŻŔŔb
íúíííí╠ěäe╩ăÁ┬ç°Ë┌╔¤╩└╝o(jĘČ)─ę▒ż╩└╝o(jĘČ)│§
úČĎĐ╚ź├Š╠ď╠ş╚ź▓┐║╦ŰŐúČŞ─×ÚĆVĚ║Á─╠ý╚╗ÜÔ─▄ď┤íú┼cÍ«¤Ó▒╚úČĚĘç°ůsĎ╗Í▒╝Ë┤ˇ║╦ŰŐď┌Ăńç°╝Ď─▄ď┤╣ęŬ(yĘęng)ˇw¤ÁÍđÁ─Ň╝▒╚íúâ╔ç°╗¨Ë┌▓╗═ČÁ─▒│ż░úČθ│÷Á─Żě╚╗¤ÓĚ┤Á─ŤQ▓▀úČĎ▓ÍÁÁ├╬Ďéâ╝Ü(xĘČ)╝Ü(xĘČ)┐╝┴┐íú╚╗°żG╔ź─▄ď┤ŮD(zhuĘún)đ═úČ│╔▒żŞ▀░║íó─┐ś╦(biĘío)▀h(yuĘún)┤ˇíóČF(xiĘĄn)îŹ(shʬ)ĂDŰyíú╝│╚íÁ┬ĚĘâ╔ç°Á─ă░▄çÍ«ŔbúČ╬Ďç°Ëđ▒ěϬŻĘ┴óżG╔ź─▄ď┤ŮD(zhuĘún)đ═Á─ĚĘ┬╔┐˛╝▄íú▀@╩ăĎ╗éÇ(gĘĘ)¤ÁŻy(tĘ»ng)╗»╣Ą│╠úČ╔Š╝░ţI(lĘźng)˲ĆVĚ║úČđŔŇű║¤▓╗═ČŇ■▓▀ĚĘ┬╔┘Yď┤úČŻĘ┴óĎ╗╠ÎĆ═(fĘ┤)ŰsÁ─íó┐╔Ň{(diĘĄo)╣Ł(jiĘŽ)Á─Íž│͡w¤Áíú═ČĽr(shʬ)úČŇű║¤ż═śI(yĘĘ)│╔▒żíóşh(huĘón)ż││╔▒żË┌╗»╩»─▄ď┤│╔▒żÍđúČŞ─ÎâĐa(bĘ│)┘N┬ĚĆŻúČĎďŰŐ┴ŽÍĂÂ╚íóŰŐâr(jiĘĄ)ÍĂÂ╚Ş─Ş´×Ú║╦đ─úČîĄăˇ╔šĽ■╣▓ÎRúČÎţđí╗»ôp║ŽĂˇśI(yĘĘ)ŞéáÄ┴ŽúČ▓óÍěđ┬║╦╦Ń╔šĽ■│╔▒żúČÎţ┤ˇ╗»Ďř╚Ű╚źă˛ŞéáÄ┴ŽúČĎď┤┘│╔╩đł÷Îď╬Ď▀M(jĘČn)╗»ÖC(jĘę)ÍĂÁ─ćóäËíú